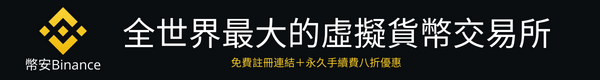翻譯/校對:龍白滔
本文為2019年12月3日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成員BenoîtCœuré先生在布魯塞爾歐洲央行代表處的講話
我很高興今晚歡迎你來到歐洲央行在布魯塞爾的代表處。看到這麼多長期的同伴和朋友,真是喜出望外。
該辦事處成立於2011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期間。如今,布魯塞爾辦事處已成為歐洲央行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我們在當地的工作人員堅定承諾和奉獻精神,這是我們對所有歐洲事務的關注和傾聽。他們的網路對於我們從布魯塞爾獲得第一手洞察力和資訊至關重要。
與我們主要的歐洲利益相關者保持高水平的合作和對話至關重要,我們不斷努力進一步提高歐洲央行對歐洲議會和廣大公眾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就是一個例證[1]。
但是,並非所有事情都掌握在我們手中。
多樣性就是一個例子。考慮到我們的最新決定,自2012年年中以來,由於我們的多元化戰略,ECB女性高階管理人員的比例從9%增加到31%。但是,所有19個國家的行長都是男性。這並不反映歐洲的現實。這損害了公眾對我們機構和單一貨幣的信任。成員國應對這種情況負責。
該辦公室的歷史與我擔任ECB執行委員會成員的任期歷史正好吻合,我的任期即將結束。我於2012年1月加入ECB,就在辦事處開業幾個月後。
這是一個動盪的八年,很可能是歐洲戰後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時期之一。這是一次信仰與鬥爭、嘗試與錯誤的旅程。
事後看來,這場危機的部分代價反映了危機之前和期間所犯的政策錯誤,以及對我們的經濟和貨幣聯盟(EMU)設計缺陷的遲遲認識。我們有責任學習和做得更好。
但是我們也可以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這些成就是顯而易見、無可爭議的。歐元區的失業率實際上已降至危機前的水平。工資正以十多年來最快的速度增長。調查顯示,歐元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公眾歡迎[2]。
這些成功並非偶然。需要作出重大努力來克服這場危機及其遺留問題。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遭受痛苦的人們。決策者們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就國家和歐元區所需的改革達成共識,(這些改革)透過穩定與增長來恢復經濟和社會福利。
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上,ECB已成功地保護了單一貨幣的完整性,克服了金融碎片化問題,使經濟走上了復甦之路。
但是,有些傷口還沒有癒合。在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經濟困難之後,歐元區的架構聽起來可能令人不安,但它仍然無法抵禦危機。
在公共債務高得令人無法接受的國家,經濟增長週期性太弱以致無法完全恢復財政空間。銀行的盈利能力仍然很低,在許多情況下,低於股本成本,反映出商業模式可持續性的風險[3]。
而生產力增長是支撐我們生活水平和社會安全網的主要組成部分,在許多成員國中仍然很低。因此,一些國家的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仍然高得令人無法接受,儘管在歐元區平均水平上取得了進展。
的確,許多其他發達經濟體也面臨著類似的挑戰。但是,潛在的增長乏力和高債務的組合在一個具有分散的財政政策和金融市場整合不足的貨幣聯盟中是有害的。
這意味著針對特定國家的衝擊仍然是整個歐元區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它削弱了對進一步一體化的政治支援。這意味著面對不利衝擊,單一貨幣政策必須承擔巨集觀經濟穩定的重擔。
新的歐洲議會和委員會的到來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可以更加果斷地解決剩餘的漏洞,重新確定重點並相應地採取行動。它為我們提供了實現這些目標的時間表。
在今晚的講話中,我將指出,我們既需要加強體制框架以使我們的貨幣聯盟更具彈性,也需要實施正確的政策以提高我們經濟的增長潛力。
我認為,靈活和富有活力的市場是歐元區的第一道防線[4]。它們是開啟持續生產率增長的關鍵,從而使貨幣政策更快地正常化。它們還減少了對巨集觀經濟穩定的需求,並遏制了有關危機管理的爭議性辯論。
第二道防線涉及可持續和促進增長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應該利用它來促進投資。債務高企的國家應調整其政策,以便在將來重新獲得財政空間,從而限制他們對鄰國帶來的風險。所有國家都可以提高支出質量。
第三道防線涉及加強我們的共同工具包——涉及新的政策工具。如果衝擊太大而無法被市場或國家財政政策吸收,則需要新的政策工具來保護貨幣聯盟的穩定。新的政策工具還提供一個防止貧困和社會排斥的安全網。
圖片來源:網路
第一道防線:整合和靈活的市場
在世界銀行營商便利度指數的前十名中,沒有一個歐元區國家。許多國家甚至沒有進入前30名。
商業環境不那麼友好的結果是歐洲的商業活力很弱。與美國相比,平均而言,歐洲國家“靜態”公司所佔份額較大,而成長中和萎縮中的公司所佔份額較小[5]。
低商業活力助長並加劇了歐元區企業間資源的錯誤配置[6]。
經驗證據表明,越來越多的資本集中在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在義大利和西班牙,目前的錯配率高於危機前任何時候[7]。
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過程的缺失,對創新和增長產生了壓力。
大量證據表明,新公司更有可能採用新技術。企業進入率、技術創造和擴散、與生產力增長之間存在著重要聯絡[8]。相對於就業份額,新公司和年輕公司也為創造就業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貢獻[9]。
疏通創新渠道要求我們改善市場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分配資源的方式。
在我看來,有三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
有效分配資源
首先,我們需要減少公司面臨的進入壁壘,尤其是在服務行業,我們需要提高破產框架的質量。
一些歐元區國家缺乏早期私人債務重組的有效框架。例如,在葡萄牙、希臘和斯洛伐克,解決破產問題需要三年多的時間。在日本、挪威和加拿大不到一年的時間[10]。
缺乏有效的破產框架也使處理不良貸款變得更加困難。它限制了抵押品的執行,並增加了銀行對“殭屍”公司寬容的風險[11]。
我們的經濟治理框架——歐洲學期——有效地通報和交換了對我們經濟的看法。
但是成員國沒有說到做到。巨集觀經濟失衡程式始終缺乏切入點,2018年針對歐元區國家的建議沒有一項得到充分落實。
在這方面,國家生產力委員會是可以加強歐洲學期討論的有益補充。
完善單一市場
其次,我們必須更好地利用單一市場提供的規模經濟。
歐元推出20年後,我們面臨著一個悖論。雖然單一貨幣最初被認為是對單一市場的補充,但在完成單一市場方面缺乏進展,現在這阻礙了經濟與貨幣聯盟的深化。
最初建立單一市場時考慮到商品的自由跨境貿易。但自那以後,我們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如今,服務業佔歐洲就業的75%以上,而1970年是45%[12]。
隨著增值和就業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作為增長引擎的單一市場日益失去吸引力。儘管有一攬子服務,但仍有5,000項國家法規保護各成員國提供不同型別的服務[13]。
這些障礙阻礙了歐洲服務公司實現規模和盈利。結果,儘管經濟體的規模大致與美國相似,但歐盟的服務公司數量卻是美國的三倍[14]。
碎片化使競爭缺失長期存在,並阻礙了圍繞效率最高的公司的健康整合。大型公司通常更多投資於人力資本和品牌資本以及無形資產,如智慧財產權、軟體和資料庫[15]。它們也比小公司更有可能出口。
因此,完善單一市場,特別是針對服務業,是我們努力提振疲軟的生產力增長的核心支柱。
這將使我們的貨幣聯盟更具彈性,並支援實際利率正常化朝更高、更積極的水平邁進。
成立資本市場聯盟
第三,如果公司要擴張和成長,我們需要擴大和深化可用於生產性投資的資金組合[16]。
歐元區的公司主要依靠銀行貸款為其債務融資。
這引起了兩個廣泛的關注。
首先是歐元區80%以上的銀行貸款仍然是國內貸款[17]。這限制了對良好信用的競爭,並加劇了主權信用和銀行信用之間的惡性迴圈,我們未能根除這種惡性迴圈。
其次,銀行常常不願為抵押品價值難以量化的無形資產提供資金,或為未來付款流高度不確定的新型可持續技術提供資金。
歐洲央行的最新研究表明,在將投資重新分配給“綠色”部門方面,股票市場比銀行更好,並且在股票市場較深的國家中,有形資產較少的創新部門增長更快[18]。
但是,在歐元區,股票市值(不足美國的五分之一)太低,無法以這種方式充當催化劑。跨境一體化程度同樣較低[19]。
我們的資本市場必須變得更深,同時,對於初創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來說,必須更容易進入。
實現真正的一體化資本市場是面對巨大的全球挑戰(例如氣候變化或數字化)時找到所需的集體對策的唯一方法。
迫切需要資本市場聯盟的另一個原因是,資本市場有助於各國更好地分擔經濟風險。
例如,在美國,對一個州的GDP的衝擊有70%是由金融市場緩衝的,而在歐元區,這一比例接近20%。資本市場聯盟可以極大地幫助分散並降低風險。
當然,如果認為不投資政治資本就可以實現資本市場聯盟,那就太天真了。例如,改進和協調國家破產法是我們法律制度的核心。但這是良好投資的(政治)資本。
私人投資者的風險分擔減少了公共風險分擔的必要性,也減少了經常隨之而來的曠日持久和激烈討論的必要性。
沒有歐洲層面對系統性中介機構和基礎設施的監管,資本市場聯盟就無法運作。
有大量的跨境溢位效應,如果出現問題,由歐洲央行直接監管的銀行將承擔大部分金融風險。歐洲監管機構、歐洲市場和基礎設施法規(EMIR)最新的改革錯失了機會。
英國脫離歐盟將對歐洲金融市場的架構產生持久影響。這加強了應對和完成資本市場聯盟的必要性。
第二道防線:健全的國家財政政策
國家財政政策在貨幣聯盟中扮演著兩個關鍵角色。
首先是支援融合、增長和資源的有效分配。
但是,在許多歐元區國家,特別是針對低收入者和次要收入者的勞動稅楔子[1]仍然過高,抑制了勞動力的供求。
透過將稅收從勞動力轉移到環境外部性或財產上,許多歐元區國家有空間以稅收中性的方式減少其稅收體系的扭曲影響[20]。
這種國家努力應輔以更緊密的稅收合作。在歐盟一級商定並執行資本收入的最低稅率,將有助於各國重新獲得減少勞動所得稅的空間,從而促進就業增長。
支援增長還意味著更加明智地支出。
歐元區的公共投資從2009年的GDP的3.7%下降到2018年的2.7%。與此同時,包括學校、醫院和道路在內的大部分公共基礎設施都迫切需要維修和現代化。
當前的利率環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透過動員投資來支援數字化並加速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從而縮小公共投資差距並增強歐洲的創新能力。
這也需要審查和增加無形資產的支出。
在過去的20年左右的時間裡,歐盟用於研發(R&D)的支出一直停滯在GDP的2%左右。在最大的歐元區國家中,用於研發、教育和運輸的公共支出約佔基本總支出的15%或更少[21]。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與環境有關的公共研發支出僅佔經合組織國家研發支出總額的1.6%。鑑於市場在環境研發方面的投入不足,而且氣候變化正在加劇,因此公共部門迫切需要介入。
財政政策在貨幣聯盟中的第二個作用與穩定和彈性有關。
在這兩個方面,《穩定與增長公約》基本上都失敗了。
事實證明這並不管用。在繁榮時期,建立足夠的財政緩衝以應對經濟衰退的必要性被忽略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它會放大順週期性。從2009年到2018年,經週期性調整的政府一級資本平均餘額,日本為-5.7%,美國為-3.6%,而歐元區為0.5%。
而且,即使在最近幾年,歐元區的總體財政立場被大體認為是適當的,它在各個國家之間的分配也是錯誤的。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沒有使用它,沒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正在嘗試發明一些[22]。
結果,從字面上看,貨幣政策必須彌補這一懈怠。
在沒有真實的反事實的情況下,容易做出假設。但是我相當相信,如果各國政府能夠更有效地執行歐洲學期的建議,歐洲央行近年來為穩定歐元區經濟而不得不採取的一些措施,以及使之(措施)成為某些成員國批評的目標,是可以避免的。
《穩定與增長公約》日益複雜化及其執行的政治化並沒有很好地為我們服務。
因此,我們需要審查規則及其執行情況。我們需要簡化它們,使其非政治化並提高國家所有權[23]。各國政府不應再選擇利用漏洞或指責布魯塞爾的技術官僚來掩飾其責任。
各國政府對選民負責。強大而獨立的國家財政委員會應向公眾清楚地說明輕率的財政行為對國家和整個歐元區穩定的潛在後果。不幸的是,我們不再缺少例子。
第三道防線:有效的區域性工具
危機表明,系統性衝擊可能超出國家財政預算提供的有效穩定的能力。
歐洲穩定機制(ESM)在運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一種危機管理工具,其本身的作用將得到進一步加強,因為做出了受歡迎的決定使ESM成為單一解決基金的後盾並引進了新的預防措施。
但是,ESM應該能夠透過以合格多數決定來在危機中採取果斷行動,並且應該根據共同體法律對歐洲人民負責——這兩專案標在當前改革提案中沒有涉及。
讓我再說一遍:政府間的決策在短期內在政治上可能是方便的,但從長遠來看會帶來很高的經濟成本。它有利於拖延,把每個決定都變成零和遊戲。
政府間危機管理增加了危機的代價,就調整負擔而言,對希臘人民而言,對希臘債權人而言,對風險敞口和潛在損失而言,對整個歐洲而言,對信任和統一而言,對整個歐洲而言,都是如此。這不是前進的道路。如果我們不從過去的危機中吸取教訓,我們將責怪自己重蹈覆轍。
這就是為什麼目前的提議只能是第一步。我們缺少的是三個相輔相成的工具。
共同的歐洲存款保險計劃
首先是共同的歐洲存款保險計劃,這是真正的一體化銀行體系和單一貨幣的先決條件。我歡迎目前在就這一計劃進行政治談判方面取得的進展。
應該在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向上並行取得進展。首先,透過激勵銀行以不干擾政府債券市場運作的方式分散其主權敞口,消除銀行—主權的厄運迴圈。
第二,加強我們的解決框架。如今,只有少數幾家銀行被認為符合公眾利益,並受制於歐洲解決方案,因此大多數銀行倒閉都可以透過十九種不同的方式來解決。這是站不住腳的。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為銀行清算建立單一的管理工具將是重要的第一步。
共同的財政能力
第二個缺失的工具是共同的財政能力,它提供了巨集觀經濟穩定,以防止或減輕系統性衝擊——也就是說,在衝擊變成全面危機之前。
當前正在實施的預算工具有一個不同的目標,即提高競爭力和趨同,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目標,儘管現有工具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但它並非旨在提供巨集觀經濟穩定。即使是這樣,它也不足以有效地做到這一點。
我們還艱難地認識到,協調國家的財政政策不會導致整個歐元區採取適當的財政立場。當前經濟增長乏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即使政府加強了協調,跨境溢位也可能太小而無法發揮作用。例如,歐洲央行的研究表明,跨境溢位可能不到初始支出的10%[24]。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歐元區需要共同的財政工具。這樣的工具將支援貨幣政策,並防止在經濟不景氣時出現順週期緊縮政策。這將增強人們對國家自動穩定器的信心,從而保護就業並最大程度地減少產出損失。
所有成功且穩定的貨幣聯盟都擁有真正的財政工具,這些工具建立在強大的法律和市場化的機制之上,確保國家一級的財政紀律。這種工具不應取代國家政策,但必須足夠大以有效地補充它們。
共同的安全資產
全球治理面臨威脅[27];為加深和整合我們的資本市場做出了巨大努力。
圖片來源:網路
結論
在歐元區危機及其直接後果的脅迫下,我們在使我們的貨幣聯盟更適合目標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我們可以為過去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今天的步驟更加不確定。當太陽照耀時,歐洲將再次無法修繕其屋頂。這種風險很高。
Jean Monnet著名的預言“歐洲將在危機中鍛造,並將成為針對這些危機的解決方案的總和”,這可能再次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要付出什麼代價呢?現在,當前的討論傾向於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循序漸進的方法。
但是在我們這個不確定的時代,採用這種漸進式方法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永遠無法到達河的對岸,並且有被河流帶走的風險。
我相信,新的歐洲領導層將找到給歐元區新方向和新步伐的決心,併為歐洲央行提供維持我們的單一貨幣健全和穩定所需的環境。
謝謝!
[1]SeeCœuré, B. (2017), “Independe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a changing world”,introductory remarks at 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U Event “Two sides ofthe same coin? Independence and accountability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Brussels, 28 March.[2]See2019 Standard Eurobarometer.[3]See ECBBanking Supervision (2019), “Risk assessment for 2020”, 7 October.[4]For anearlier contribution, see Cœuré, B. (2018), “The euro area’s three lines ofdefence”,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Deepening of EMU”, Ljubljana, 2 February.[5]SeeBravo-Biosca, A. (2017), “Firm growth dynamics and productivity in Europe”,inRemaking Europe: the new manufacturing as an engine for growth,Bruegel.[6]SeeCœuré, B. (2017), “Convergence matters for monetary policy”, speech at theCompetitiveness Research Network (CompNet)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firmsize, productivity and imbalances in the age of de-globalization” in Brussels,30 June.[7]Ibid[8]See,for example, Anderton, R., Di Lupidio, B. and Jarmulska, B. (2019), “ProductMarket Regulation, Business Churn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ECB Working Paper No 2332. See also Canton, E.(2016), “Driver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EU: the role offirm entry and exit”,Quarterly Report on the EuroArea, Directorate Gener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EuropeanCommission, vol. 15(1), pp. 25-35.[9]SeeCalvino, F., Criscuolo, C. and Menon, C. (2016), “No country for young firms?Startup dynamics and national policies”,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olicyPapers, No 29, OECD Science.[10]SeeConsolo, A., Malfa, F. and Perluigi, B. (2018), “Insolvency frameworks andprivate deb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CB Working Paper No 2189.[11]SeeAndrews, D. and Petroulakis, F. (2019), “Breaking the shackles: Zombie firms,weak banks 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Europe”, ECB Working Paper No 2240.[12]SeeCœuré, B. (2019), “The rise of servic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policy”, speech at the 21st Geneva Conference on the World Economy, 16 May.[13]SeeEconomist (2019), “Briefing: The economic policy at the heart of Europe iscreaking”, 12 September.[14]Ibid.[15]See, forexample, Crouzet, N. and Eberly, J. (2018), "Intangibles, Investment, andEfficiency",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426-31. In Italy, for example, approximately three-quarters of the productivitygap to the global frontier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national frontierfirms – while actually quite productive in global terms – are relatively smallcompared with those at the global frontier. See Andrews, D. and Cingano, F.(2014), “Public Polic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Firms in OECDCountries”,Economic Policy, Vol. 29 (78), pp.253-96,[16]Seealso Cœuré, B. (2019), “European capital markets: priorities and challenges”,dinner remarks at 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Frankfurt am Main, 25 June.[17]Despitesignificant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to develop a more coherent policyframework for cross-border banking, namely with the single rulebook and thecreation of European supervision and resolution.[18]See DeHaas, R. and Popov, A. (2019), “Finance and Carbon Emissions”, ECB WorkingPaper No 2318.[19]Just20% of euro area equity holdings are issued in other euro area countries. Forbonds, the share is 30%.[20]See,for exampl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Affairs (2017), “Financing labour tax wedge cuts”, technical services note tothe Eurogroup.[21]SeeEuropean Fiscal Board (2019), Assessment of EU fiscal rules, with a focus onthe six-pack and two-pack legislation, August.[22]See the2019 Annual Report of the European Fiscal Board.[23]Forproposals, see, for example, European Fiscal Board (2019,op. cit.); Eyraud, L. and Wu, T. (2015), “Playing bythe Rules: Reforming Fiscal Governance in Europe”, IMF Working Paper 15/67; andDarvas, Z., Martin, P. and Ragot, X. (2018), “European fiscal rules need amajor overhaul”,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Issue18, October.[24]SeeAlloza, M. et al. (2019), “Fiscal spillovers in a monetary union”,Economic Bulletin, Issue 1, ECB.[25]For anoverview, see Giudice, G., de Manuel Aramendía, M., Kontolemis, Z. andMonteiro, D. P. (2019), "A European safe asset to complement nationalgovernment bonds,"MPRA Paper95748,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26]Alternatively,this could be achieved by lifting the zero risk weight that government bondscurrently enjoy under the prevailing regulatory framework.[27]SeeCœuré, B. (2019), “The euro’s global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 a monetarypolicy perspective”, speec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ity,15 Febru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