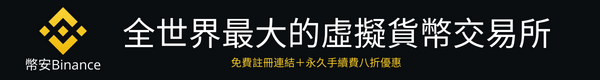桃花潭按
發表本文是因為《朱嘉明 | 改革四君子之一談中國改革四十年經濟思想史》中提到“匈牙利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Polanyi)的「自我調節市場」(self-regulatingmarket)理論”。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5日—1964年4月23日),是匈牙利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是20世紀公認的最徹底、最有辨識力的經濟史學家。當法西斯主義興起時,他離開了出生的匈牙利,成為英國公民。在其學術生涯中,曾先後在牛津大學的本寧頓學院和倫敦大學教書。著有《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大轉型》和《達荷美和奴隸貿易》(與A.羅特施泰因合作)等作品。
本文描述了Polanyi鉅著《大轉型》的思想源泉,結合人類學史和古代史,討論了青銅時代的(信用)貨幣起源、債務經濟處理、監管和市場並行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必要性。深刻批判了極端的“自由市場”和商品貨幣理論服務於壟斷市場力量、寡頭、銀行階層的本質,指出貨幣是法律公共創造物並服務於社會目標的本質。而不受監管的市場力量和逐利行為導致社會體系純粹為“金錢收益最大化”的財務目標而執行,導致經濟的兩極分化和緊縮。深刻批判了西方文明在處理其經濟學史時的虛偽,刻意將曾經青銅時代的信貸、債務和財產關係的制衡機制從西方文明主線剝離,而只留下今天的“債務神聖性”和債權人導向的法律哲學。文章最後結論,社會主義本質上是“自覺地將市場服從於民主社會而超越自我調節的市場”。
貨幣金融領域最大的謬誤之一是貨幣起源於物物交換,經濟學領域最大的謬誤之一就是自由市場是完美、中性、與生俱來的。透過回顧Polanyi學術思想形成、發展和延伸的過程,結合人類學和歷史學資料,我們可以瞭解到,人類最早的貨幣體現了國家權威,起源於公元前三千年兩河流域的宮殿和寺廟經濟,並且當時已經有成熟的手段來處理週期性的債務危機,透過“清潔石板”購銷掉無法償還的公共債務。人類歷史上,任何時代的經濟體都是混合模式,包含了互惠、再分配和市場交換等不同交換體系,並且歷史上大部分時候貿易和收入都是受到監管的。
本文為理解中國“為公眾利益監管金融”的哲學、以及中國在處理債務危機時的公共政策選項(購銷無法償還的公共債務以恢復經濟體的執行和韌性)提供了可信、充分的人類學和歷史學證據。這對理解中國監管近期加強監管以削弱大型科技公司的金融壟斷和維護經濟穩定和公平的競爭市場,至關重要。本文證明,金融治理的中國模式,並非新鮮事物,它體現了人類文明祖先的古老智慧,並且擁有完整和堅固的理論依據,我們完全可以驕傲於“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文字量很大,相對也比較晦澀,但對形成正確的貨幣、經濟觀至關重要。
本文也是理解《論數字貨幣八大沖突》之核心論點的基礎。
戰後貨幣崩潰對《大變革》的啟示
在一戰的餘波之中,Karl Polanyi的形成期是一段貨幣動盪的時期。美國第一次成為債權國,並要求償還Keynes警告說不破壞歐洲金融體系就無法償還的戰爭債務。(Hudson,超級帝國主義,1972年,總結了這個時代。)法國和英國讓德國承受了無法持續的高額賠償債務,同時透過堅持金本位制對本國經濟實施緊縮。法國的Jacques Rueff和美國的Bertil Ohlin認為,德國可以用黃金支付任何水平的賠償金,而盟國也可以支付他們的外幣武器債務,方法是將失業率提高到足夠高的水平,從而使其工資足夠低以使得其產品足夠廉價,從而產生足以償還債務的貿易盈餘。
大多數國家遵循“硬通貨”的理念,即透過將貨幣可兌換為黃金,貨幣是一種商品或可用作商品的代理。最著名的倡導者是奧地利的Ludwig von Mises和Friedrich von Hayek,其結果是貨幣緊縮。這是1815年之後發生事情的重演,當時銀行家David Ricardo堅持認為,面對任何既定的外債償付或軍事補貼,迴歸金本位將恢復平衡。他聲稱,任何此類支付赤字都會自動以接受國對“資本支付”經濟體的進口需求的形式被回收。結果是沒有這樣的平衡。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實施金本位制時,各經濟體為了降低物價和工資而缺乏貨幣,而徒勞地試圖還債。Rueff、Ohlin和Hayek認為,將通貨緊縮和貧困強加給債務國將(而且應該)代表一種穩定的均衡。
所有東西——包括貨幣、土地和勞動力——都被視為一種商品,其價格將由供需公平決定,但“需求”會因無限制地向債權人償還債務而受到侵蝕。貨幣的創造不受政府控制,因為正如Margaret Thatcher對Hayek意識形態的詮釋:“社會是不存在的。”只有(而且應該)只有一個市場——一個不可避免地由金融財富、銀行和產權人主宰的市場。
Polanyi將戰後的崩潰和大蕭條歸咎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強加。他寫道,20世紀20年代見證了經濟自由主義的聲望達到頂峰,並預測,“毫無疑問,我們的時代將被視為自我調節市場的終結”(Polanyi,1944:148)。他預計,實施這種狂躁的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混亂將證明如下斷言的謬誤:即市場具有自我調節能力,可以在不造成經濟破壞、失業和貧困的情況下“脫離”其社會監管環境。
為了證明公共監管的必要性,Polanyi對貨幣、信貸和土地使用的組織模式進行了回顧,哪些模式能夠持續繁榮,哪些模式失敗了。他拒絕接受他認為的Marx的序列的生產模式,強調交換模式。他指責Marx的一系列“歷史上站不住腳的階段”,從“經濟的特徵是由勞動的地位決定的信念”(Polanyi, 19567: 256),從古代奴隸制和高利貸,到封建主義的農奴制和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Marx關注從封建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的轉變,把勞動力從土地上趕走,變成為僱主工作的僱傭勞動,Marx的目的並不是要回顧土地所有制的歷史。Polanyi敦促說,“土壤融入經濟應該被視為同等重要。”“在封建制度和金箔制度下,”Polanyi寫道,“土地和勞動力構成了社會組織本身的一部分(貨幣還沒有發展成工業的主要元素)。”土地的分配是維持軍事、司法、行政和政治制度的基礎;它的地位和功能是由法律和習慣規則決定的。(Polanyi, 1944: 69)政府的正確任務是將其租金用途的規則社會化——稅收,還是支付給食利者?
在《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Marx將地租和高利貸追溯為封建時代的殘餘物,他期望工業資本主義透過使經濟從剝削地租的地主和高利貸銀行業中解放出來以消除這種“生產的弊端“。相反,這些食利者利益集團重新控制了經濟,他們揮舞著自由市場個人主義的旗幟,反對公共監管。將貨幣收益理想化,而不考慮其對公共利益的影響,銀行家和其他食利者將“自然”或“純”經濟定義為不考慮社會福利而對價格或市場進行監管。經濟被視為一個人人自由的市場,而不是一個以穩定社會和提高生活水平為首要任務、調節財產、信貸和債務的社會體系。
透過將公共監管權力描述為“非自然的”, 自由市場政策假設,將財產所有權、信貸和債務的規則交給私人財富是自然和可取的。現實是,缺乏社會監管的“自然”市場從來就沒存在過。所謂的自由市場,只不過是一種對地位的爭奪,優勢掌握在最富有的個人手中。他們的利益在於儘量減少公眾對其尋租、信貸和止贖以及其他商業活動的監督和徵稅。
Polanyi意在證明,將勞動力、土地和貨幣政策置於不受監管的“自由市場”是多麼愚蠢。真正的問題是市場經濟將會是什麼樣的,誰將是它們的主要受益者或犧牲品。《大變革》相信封建主義和英國早期的工業資本主義仍然執行《濟貧法》(注:中世紀晚期的英國處理流民與貧困問題的法律)來保持廣泛的社會目標和規章制度,而不是把勞動和土地當作商品扔到狼群(富人)中。即使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重商主義國家也同樣反對將勞動力和土地商業化的想法,這是市場經濟的先決條件。……重商主義雖然傾向於商業化,但從未攻擊這項保障措施,它保護這兩個基本生產要素——勞動和土地——不成為商業物件”(同上:70)。
從古代到整個封建歐洲,土地構成了普遍的稅基。與有生產成本的正常商品不同,土地是自然免費提供的。他解釋說,土地、勞動力和貨幣顯然不是商品。勞動力是生命,“土地只是自然的另一個名稱”,不是由勞動生產的,因此沒有生產成本(古典價值),其租金是合法的財產主張。但市場給它一個價格,以便轉讓所有權,使地主無需工作就能獲得租金收入(同上,72)。雖然土地的地價主要是由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創造的,但土地所有者仍在為自己保留土地租金而鬥爭。這使得政府無法將土地租金作為稅基納入公共領域。在古代,止贖的債權人和大投資者迫使小農離開自己的土地,剝奪了政府的稅收、徭役勞動和自由公民軍。
當Polanyi把貨幣稱為一種虛構的商品時,他反對透過掛鉤貨幣的供應到黃金的供應來使貨幣稀缺的想法,這就像模仿商品,就好像貨幣是易貨體系的一部分一樣。它還賦予了債權人壓倒性的權力來控制經濟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在勞動力和土地方面,它將工資水平和農作物價格壓低到基本收支平衡的需要之下,而政府被剝奪了為僱傭勞動力創造信貸的能力。他批評Ricardo“向19世紀的英國灌輸了這樣一種信念,即‘貨幣’一詞意味著一種交換媒介,紙幣可以輕易地兌換成黃金(同上:196)。鑑於黃金供應有限,這一政策導致了通貨緊縮。當各國在戰時通脹後恢復黃金可兌換性時,價格和工資的下跌對債務國不利。1815年後的英國和19世紀70年代後的美國都出現了這種情況。當時美國試圖降低價格,從而使黃金價格——因此以及工資和商品價格——回落到內戰前的水平。其結果是長期的經濟蕭條,導致土地和其他財產從債務人轉移到債權人手中。
Polanyi偏好的替代(理論)是透過讓貨幣成為法律的公共創造物以讓貨幣服務於社會目標。這種代幣沒有內在的生產成本,"而是透過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產生的”,因此不是一種具有最終生產勞動成本的商品:“最後,實際貨幣只是購買力的象徵,一般來說,它根本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透過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產生的”(同上:72)。
Polanyi的奧地利對手辯稱,公共貨幣創造、社會支出計劃、監管和補貼扭曲了定價市場本應高效的“自然”經濟。實際上,這意味著低工資和向富人轉移土地。不受監管的市場力量和逐利行為導致社會體系純粹為“金錢收益最大化”的財務目標而執行,使土地、勞動力和貨幣受制於債權人的偏好,而不是有利於負債的多數人。Polanyi聲稱,正是為了防止這種經濟兩極分化和緊縮,“監管和市場……共同成長。”貿易和收入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受到監管的,這是因為“一般來說,經濟體系是被社會體系吸收的”(同上:68)。
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追求金錢的行為破壞了農業和工業的穩定。法國堅持金本位,實行緊縮政策,英國的類似政策導致1926年全國大罷工。Polanyi說,其寓意是:
讓市場機制成為人類命運和他們的自然環境——甚至是購買力的數量和使用——的唯一主宰,這會導致社會的毀滅。……購買力的市場管理會定期清理企業,因為貨幣短缺和過多對企業造成的災難,就如同原始社會的水災和旱災一樣。(同上:73)
Polanyi在哥倫比亞的跨學科專案
1944年出版的《大變革》(Great Transformation)導致Polanyi(Polanyi)在哥倫比亞大學(Colombia University,1947-53)的任命。他組織了一批人類學家和古代歷史學家,回顧了非市場社會如何塑造他們的勞動、土地和貨幣關係。這為定價“自由”市場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一直存在的假設,提供了一項經驗的替代理論。
該組織對自由市場歷史版本的替代理論的首次研究是《早期帝國的貿易和市場》(1957年),這是20世紀初所謂的原始主義者和現代主義者之間爭論的結果。現代主義者對歷史的解讀認為,追求自我的個人自發地創造了貨幣和企業,沒有酋長、宮殿和寺廟在其中發揮作用。反對這種觀點的Karl Bücher(1847-1930)反駁說,古代經濟並不是按照現代個人主義的路線組織起來的。他“反對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因為這些理論有一個狹義的、有時間限制的經濟概念,他們認為這個概念適用於所有歷史時期”(Polanyi,1962:164)。
與Bücher一樣,Polanyi拒絕了這些重建:他們讀起來像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進入時間機器並回到新石器時代按照現代方式組織信貸和市場。他的追隨者Johannes Renger(1972)觀察到,如果有任何古老的經濟體遵循那種理想化的教科書模式,那麼債務人將會逃離,或投奔承諾免除其債務的競爭對手那裡。互助及其對暴利的相關限制是生存的先決條件。酋長們被期望是慷慨的,保護弱者和需要幫助的人。
Polanyi在闡述《大變革》中形成的思想時,借鑑了人類學和古代歷史,表明貨幣的“義務在這裡通常不是從交易中產生“以在市場上交換商品。它們更多地與稅費、欠債和其他義務的支付有關:“將大麥、石油和羊毛等主要原料等價起來,這對必須支付的稅費或租金,或者對要求的可替代的配給或工資,是至關重要的”(Polanyi,1957:264f)。
Polanyi把市場交換刻畫為三種不同的交換體系之一:互惠(禮物交換)、再分配和“市場”交換。“個人之間的互惠行為只有在對稱的組織結構(如親屬群體的對稱系統)被賦予時,才能使經濟一體化。”這種對稱性可能會因“市場崛起為經濟中的主導力量”而受到干擾,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糧食透過交換被調動起來,勞動力已變成了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購買的商品”(同上:225)。他並沒有看到這是在公元前1800年古巴比倫時期已經發展起來的,或者說債務是使富人從小農手中獲得土地的主要槓桿。債權人通常讓自己被收養為負債的土地所有者的“兒子”,這樣他們就可以根據已有的規則在適當的時候繼承土地,把土地交給世襲家庭。
Polanyi總結了他的希望,即透過恢復“讓人想起早期經濟組織的形態”,社會將擺脫市場脫離其社會背景的困境。在一個新的再分配經濟中,社會需要透過管理關鍵價格和收入來重新嵌入商品和服務的市場結構。這種再分配的前提是社羣存在一個分配中心,比如早期的宮殿或寺廟,以及當今世界的民主政府辦公室。
Polanyi對亞述學的影響
Polanyi的兩位追隨者Leo Oppenheim和Johannes Renger將蘇美爾和巴比倫尼亞描述為再分配的寺廟和宮殿經濟。Renger在1984年關於宮殿背景下貿易和企業的文章展示了這些大型機構在資源分配和定價方面的作用。為了對他們自己的經營和與整個經濟體的交易進行前瞻性規劃,宮殿和寺廟需要在合併的整體資產負債表中對穀物租金和費用的支付以及貿易、放牧和其他活動進行估價。他們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創造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貨幣。
Polanyi將再分配描述為一種經濟範圍內的交換模式,就好像美索不達米亞不可能既是再分配又是市場經濟一樣,意味著美索不達米亞在一個價格差異很大的行業,尤其是城市之間,也沒有繁榮的逐利貿易。這使他容易受到批評,最著名的是Morris Silver。後者列舉了私人牟利交易的例子,例如Cappadocia的亞述人,還有證據表明價格常常超過王室公告規定的價格。(Silver, 1983年;Silver, 1995年)。
Renger描述了烏爾三世新蘇美爾第三王朝(公元前第三個千禧年晚期)的宮殿需求中,有多少是由企業家為他們所代理的[王室]家族處理的(Renger,1994:197)。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商業交易,通常是由王室委託,但也會以加價出售給經濟體的其他部門。他們還自己出借,併為宮殿收取稅費。再分配的宮殿經濟和價格更為靈活的不太正式的經濟部分之間的混合使得通常很難區分“公共”和“私人”,因此很難區分再分配和“市場”交換、貸款和利息、租金或其他義務(Yoffee,2003:6)。
在美索不達米亞,為市場和信貸的企業交易與宮殿再分配、管理定價和禮物交換共存,他們各自存在。美索不達米亞並不是唯一一個混合經濟體。在過去的五千年裡,幾乎每個社會都是多層次的,同時具有Polanyi的三種交換方式。即使在今天,家庭和朋友之間的禮物交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管理價格也與市場交換並存。
然而,追求貨幣收益通常是“嵌入”在一個整體的社會環境中。皇家清潔石板的“正義與公平”宣告取消了累計的穀物稅和其他土地債務,解放了奴僕,恢復了小農被沒收的土地。(我在“…並免除他們的債務”中提供了此類行為的歷史:從青銅時代的金融到禧年[2018年])的借貸、沒收和贖回。這就保留了一個自由公民在軍隊服役和提供徭役,而不是陷入對非官方債權人的永久債務束縛中。
過去幾十年的亞述研究表明,美索不達米亞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現代的。正如Dominique Charpin總結的那樣,Polanyi認為漢謨拉比的巴比倫王國是一個非市場經濟體,這一觀點是在沒有現有文獻的情況下從理論上形成的。近年來出版的許多文獻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價格波動是市場的特點。這些術語很容易不合時宜地使用,並導致誤解的產生。(Charpin,2003:196)。
這種誤解在半個世紀前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Polanyi最有影響力的追隨者之一,Moses Finley,把古代近東排除在西方文明的敘述之外。在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紅色恐慌期間,Finley因為是共產主義者而在美國被趕出了教育領域。Finley堅持認為,西方文明是從原始社羣發展而來的,這些社羣的酋長制度直接演變成古希臘和羅馬城邦。他認為:
近東經濟以大型宮殿群或寺廟群主導,這些建築群擁有大部分可耕地,幾乎壟斷了任何可以稱為“工業生產”的東西和對外貿易(包括城市間貿易,不僅僅是與外國的貿易),並透過一個單一複雜的、官僚的、記錄的操作,組織了社會的經濟、軍事、政治和宗教生活。“定量配給”,從廣義來講,是我能想到的一個詞來很好描述這種操作。……因此,排除近東不是武斷的……(Finley,1985:28)
這種對近東經濟的排斥基於錯誤的理由,即它們沒有企業家心態。這忽視了它們的“混合”特徵。它的二元論態度集中體現了Polanyi的一些追隨者傾向於將社會視為“社會”或“自由市場”,好像商業企業和計息債務與公共監管和管理定價不相容。Finley將其視為原始主義者的死衚衕,就像Karl Wittfogel對“東方專制主義”的解釋那樣,認為灌溉的經濟體具有極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式的專制主義。事實上,宮殿是企業和富有彈性的混合經濟的贊助者,後來為古典希臘和羅馬提供了商業企業和計息債務的基本技巧。
在評論Finley的二元論觀點是如何被商人和投資者的大量文獻所質疑時,Steven Garfinkle指出:
因此,當把“原始”一詞用於美索不達米亞的經濟時,就變得特別令人反感了……對Finley來說,古代近東不僅是原始的,而且很奇怪,因此,它不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透過將古代近東置於西方經驗之外,Finley能夠證明它被排除在古代歷史之外是合理的;但前提是我們要把“古代史”理解為專門適用於經過仔細篩選的“西方”起源。(Garfinkle,2012:6f)
亞述學家已經證明了追求金錢利益的企業家的作用,這些企業家首先出現在宮殿經濟中,管理皇家企業以及與其他城市和地區進行貿易。事實上,貿易和私有化是如何發生的?(Garfinkle,2004a;2004b)。
新經濟考古學是Polanyi方法的產物
新經濟考古學在許多方面都是Polanyi哥倫比亞大學小組的產物,它強調市場幾乎總是受到監管,以避免長期失衡和破產。這一學派超越Polanyi之處是強調債務的作用,也強調了美索不達米亞宮殿經濟和個體商人之間的共生關係所產生的企業的作用。古代近東經濟國際學者會議(ISCANEE)透過對青銅時代宮殿和寺廟企業、土地保有權、債務、早期貨幣發展以及商業信貸和農業高利貸之間的原始區別的調查,試圖填補文明史上的空白。
我們的小組始於1994年,當時我和哈佛大學人類學系Peabody博物館的Karl Lamberg-Karlovsky合作,組織了一系列座談會,我們邀請了主要的亞述學家、埃及學家和考古學家來探討文明起源的商業和貨幣實踐,以及早期社會是如何做到的防止個人債務破壞經濟穩定和兩極分化,就像希臘和羅馬就是這樣。我們小組已就土地使用權與城市化、貨幣與利息、勞動組織、商業與企業等問題編寫了五卷學術討論會文集。它們共同展示了青銅時代近東混合經濟體如何創新商業企業的基本技術。
第一次會議於1994年11月在紐約大學舉行,主題是《古代近東和古典世界的私有化》(1996年由哈佛大學Peabody博物館出版)。它側重於大型機構與其他經濟部門之間的關係,當時宗族單位擁有土地,宮殿主導商業活動,而寺廟則充當今天所謂的公用事業,向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提供手工藝品出口。
在那次座談會之後,又舉行了兩次會議,第一次是1996年由紐約大學主辦,第二年由位於聖彼得堡的俄羅斯東方研究所主辦,主題是《古代近東的城市化和土地所有權》(Peabody博物館,1999年)。其撰稿人指出了高利貸在破壞宗族土地保有權方面的作用。歷史上,債務一直是將土地集中在止贖債權人手中的槓桿。
這兩卷書為我們打算成為本系列的巔峰之作奠定了基礎,論述了青銅時代統治者廢除農村高利貸債務和欠款以維護經濟穩定的邏輯。第三次討論會於199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古代近東的債務和經濟復興》(CDL出版社,2002年)。與當時廣泛流行的現代主義信仰不同,現代主義者認為“清潔石板”是過去的烏托邦理想,而我們的研究小組記錄的法律記錄顯示,這些皇家赦免確實是在實踐中得到了執行。
原因很清楚:幾千年前,社會本來會屈服於奴役和土地壟斷,如果他們認為“自由市場”意味著償還個人債務的神聖性。羅馬是第一個不取消農業和個人債務的主要社會。對它的寡頭政治而言,“財產的神聖性”是指可以對債務人的自給自足的土地和其他財產進行止贖。
我們的小組被認為是對Polanyi這一代人工作的延伸,這次座談會包括參觀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論文件案。我們得到了如此積極的迴應,以至於我們於2000年在大英博物館舉行了第四次座談會,主題是貨幣的起源,《創造經濟秩序:古代近東的記錄儲存、標準化和會計發展》(CDL出版社,2004年)。下一次座談會於2005年在德國舉行:《古代世界的勞動》(ISLET,2015)。這五卷書合在一起,勾勒出了近東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新畫面,擴充套件了Karl Polanyi的基本見解。
寺廟和宮殿在貨幣起源中的作用
貨幣起源於公元前三千年美索不達米亞的大型機構發展起來的會計實踐,用於對他們之間和他們與經濟體其它部門之間的交易進行計價,並以支付稅款、費用和商品和服務為主要用途。白銀用來計算商人為託運原材料和奢侈品而交易所產生的債務(宮殿通常是主要客戶),而作物年的土地租金、服務費和給耕種者的預付款都是以穀物計量。大多數交易都透過信貸進行,在作物季結束時在打把場結算,或在規定的貿易冒險期結束時結算。宮殿接受白銀和穀物,使它們成為整個經濟體中的一般支付手段。
Polanyi強調政府合法創造貨幣。亞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指出,希臘的鑄幣術語nomisma,是基於詞根nomos(我們的貨幣學術語“錢幣學”numismatics的根源),意思是法律。貨幣化的商品被當做貨幣,是因為被接受作為稅款支付,或作為宮殿和寺廟商品和服務的費用支付。現代政府可以支付社會支出,併為經濟增長提供貨幣,只要他們徵稅為這些貨幣創造使用價值即可。
那些追隨奧地利經濟學家Carl Menger和他在1871年編造的貨幣寓言的人士忽視了稅收、債務償還和公共貨幣創造。在他的描述中,貨幣出現在易貨貿易的個人中間,他們更喜歡用輕便的小東西作為交換工具,最終也用於儲蓄和財富積累(Menger,1871/1892)。後來的奧地利人譴責《貿易和帝國》是對這種個人主義和完全反政府理論路線的威脅。Fritz Heichelheim稱這本學術著作是“業餘”的,也是“一本非常令人遺憾的書”,他說這本書不應該出版。“系統的經濟理論家將不得不拒絕或重塑這本書中所表達的關於經濟歷史的觀點”(Heichelheim,1960:108)。
Heichelheim早些時候創造了一個“私營企業”寓言,其中古代寺廟和宮殿沒有任何作用。他認為,在新石器時代,利息起源於當債權人“預支”動物和作物種子以換取盈餘的一部分。他關於早期利率反映生產力、利潤率和風險的“現代主義”假設在今天甚至還不成立,但它被及時應用,彷彿它解釋了利率的起源(Heichelheim,1958:54f)。
個人主義的貨幣和利息的創造神話描繪了種植者和工匠相互交換他們的產品,併為借用牛和穀物以產生盈餘而要求利息,債務人從盈餘中支付利息給債權人。據說,更富裕的債權人更喜歡用金屬片作為緊湊和不易腐爛的儲蓄手段。沒有說明的是這些金屬應該來自哪裡。整個古代,金屬都是在寺廟中提煉出來的,以保證其純度,而皇宮則支援了獲得金銀的貿易。進口白銀是最負盛名的物品,皇室對寺廟的捐贈確立了它們的社會和禮儀地位。宮殿使白銀成為貿易和商業合同的主要媒介,也是管理宮廷企業的主要媒介。
個人以物易物不可能是一個現實的解釋。從巴比倫的“智慧文學”到《聖經》,有一長串譴責商人和債權人使用虛假度量衡的文章——借貸或出售時用輕的秤砣,債務人償還和購買時用重的秤砣。這一文學記錄清楚地表明,即使商品貨幣也決不能留給私人個人,因為這樣做會為債權人和商人開啟歪門邪道的大門。在市場交易中,有效的公共權力一直是遏制欺詐和保證公平交易的必要條件。這就是為什麼欺詐者試圖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利用自由市場的虛偽口號來摧毀政府的監管能力。
除了寺廟和宮殿,還有誰能提供誠實的標準?如果沒有他們對標準度量衡的監督,證明貨幣金屬的純度,以及對欺詐的制裁,貨幣交易就不可能可行。這就是為什麼從美索不達米亞到羅馬在寺廟裡鑄造銀。我們所說的“貨幣(money)”這個詞來自羅馬的Juno Moneta神廟——“華納”(warner),它的鳴雁警告羅馬有入侵的威脅。(moneta一詞最初指的是預兆。)
如果不認識到公元前3000年寺廟和宮殿的催化作用,就不可能解釋貨幣的起源和早期發展。除了為宮殿經濟欠下的債務計價外,貨幣還為宮殿和寺廟的成本核算和資源分配提供了依據。這些大型機構的就業和生產規模遠遠超出了人際交換的規模。作為再分配經濟的一部分,蘇美爾神廟為他們的作坊提供勞動力來編織紡織品和製作其他手工藝品,宮殿將這些手工藝品用於出口以獲得白銀和其他原材料。
寺廟根據標準的30天月份,在他們的60進位制的日曆分配系統中,為銀的謝克爾和米納斯(古代埃及、希臘等的重量單位)以及穀物的“蒲式耳”(容量單位)建立並管理了度量衡,以便於分配工資。銀(按規定純度鑄造)和穀物被指定為在收穫時支付稅款、費用和其他債務的主要手段。為了向宮殿或其他鄉村債權人支付費用和稅款,一謝克爾銀的價值被設定為相當於一古爾“夸脫”(容量單位)穀物。(可以肯定的是,穀物在城市間的交易價格可能會在作物歉收時急劇上升,比如在新蘇美爾人的烏爾三世帝國末期)。
*******正如Lamberg Karlovsky(2009)所指出的那樣,“在世襲制國家中,私人領域和官方領域之間幾乎沒有職能上的劃分。官職起源於統治者的家庭”。在這種關係中,利潤不是目的,而穩定的連續性是。易於記賬和穩定的價格關係是不允許價格變動的邏輯。而白銀是最主要的奢侈品,不受供求關係或成本利潤計算的影響。這句話從哪裡開始?
此外,互惠和再分配是按照與市場經濟一樣合理的路線組織的,但邏輯是不同的。它基於建立一個規則和秩序的體系,而不是靈活的定價市場。
第三個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的進口無論是改變供求關係還是價格顯著變高或變低都不會影響價格。市場價格要麼被管理,要麼一旦確定,就以慣性繼續下去,除了作物價格的季節性變化或對作物歉收的反應外,對供求變化幾乎沒有反應。此外,不像今天的貿易狂熱者所主張的那樣依靠貿易來獲取日常必需品,美索不達米亞的主要進口商品(它們的價格、度量衡以及因此貨幣等價性首先被記錄在案)包括生產商的商品,如礦石、錫或銅,或諸如黃金、白銀和豪華寶石等奢侈品。主要出口品是寺廟和宮殿作坊(主要是受供養的戰爭寡婦及其子女)編織的名貴紡織品,以及如刀具和鑿子等功能性物品。“奢侈品貿易(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遠端貿易中佔很大比例——從考古發現可以看出)只涉及很小一部分人口。”
*******
這些發現與Polanyi早期合作者Leo Oppenheim的發現是一致的,他認為美索不達米亞的經濟既不是建立在定價的“自由”市場上,也不是原始的,而是一個混合經濟體,在大型機構內部實行價格管理,以便自己記賬,並對欠他們的款項進行計價。
債務的主導作用
鑑於長期以來債務造成的問題,對社會如何監管信貸和債務的分析應該是我們理解貨幣的核心。鑑於美索不達米亞典型的債務是欠宮殿、寺廟和官僚機構的徵收者的——費用和稅收、被征服民族的貢品、商人根據皇宮的委託或命令列事——對早期貨幣、債務和財政政策的分析必須在邏輯上結合在一起。
主流經濟學家將信貸(以及隱含地,欠款和貸款)視為始終具有生產性和幫助性,而不是剝削性和社會不穩定。他們把政府為取消債務而進行的干預描述為導致經濟危機,而不是將民眾從貧困和混亂中解救出來。這種教條主義的做法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實踐中,“債務安全”意味著讓拖欠債務的古代債務人失去土地和人身自由。這意味著他們的財產權不安全。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正如Ricardo認為所有外債都可以透過自動互惠需求來償還一樣,現代經濟週期理論家將均衡描述為工資和價格靈活性的結果。要將普遍的債務人財產止贖視為一項可行的政策,需要假定經濟體以穩定、公平和高效的方式進行自我調整。現實情況是,放鬆對債務和土地所有制關係的管制,會導致債務緊縮。
把信貸和金融業務計劃描述為只有積極的經濟影響,會產生歷史的歪曲。僅把債務及其利息費用看作是個人之間的討價還價,就無法認識到整個經濟範圍內的債務負擔往往會超過償付能力的範圍。它對金融寡頭在缺乏公共制約的情況下的行為視而不見。對金錢的貪婪得到了讚許,似乎確保債權人的索償是組織經濟最合理的方式。這意味著,政府不需要從市場“外部”採取行動,例如透過“清潔石板”的方式來扭轉舊巴比倫時期(公元前2000-1600年)侵蝕傳統土地保有權的農村高利貸的影響。
縱觀歷史,債務一直是土地私有化和使人口淪為奴役的主要槓桿。美索不達米亞透過將債權人的權利服從於王朝生存的目標之下,成功地推遲了這種兩極分化的動態。但古典希臘和羅馬缺乏皇室清潔石板的傳統。那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Livy、Plutarch和Diodorus描述了債務如何剝奪了羅馬人的公民權的,然而,一項現代調查卻引用了一個看似全面的210個原因的清單,後人一度將羅馬衰落歸咎於這些原因,但清單中甚至沒有包括債務(Demandt,1984年)。
西方文明將經濟學從其社會背景中剝離出來
在公元前1200年後,愛琴海的記錄消失了。六個世紀後,當他們再次出現時,希臘和義大利的酋長和軍閥已經採用了敘利亞和腓尼基商人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帶來的計息債務的做法。然而,最關鍵的是,他們有選擇地採納了這種做法,缺乏將債務人從奴役中解放出來並恢復被債權人止贖土地的權利的“清潔石板”。希臘和羅馬的寡頭政治使信貸私有化,擺脫了皇室的凌駕。
“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從“中間”挑選了西方文明的脈絡,只選擇了在信貸、債務和財產關係從維持近東經濟騰飛的制衡機制中脫鉤和脫節後的部分。這就好像青銅時代取消農業債務是一條死衚衕(甚至是“東方專制主義”)。這種排斥助長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從古典希臘和羅馬到今天債權人導向的緊縮和放鬆監管的浪潮,“債務的神聖性”和止贖權是達爾文自然選擇和適者(即最富有者)生存的原始結果,而不是導致社會解體。
統治者一方面試圖讓公民免於債務束縛,另一方面債權人以宮殿為代價謀取私利,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一直是貫穿文明史的一條主線。西方經濟的顯著特點是信貸、土地自然和公共基礎設施的私有化。這是千年前真正的彎路。古代社會把生存所需的土地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美索不達米亞統治者沒有將勞動力和土地所有權商品化以使債役和止贖不可逆轉,而是宣佈清潔石板的做法,以避免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財務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後來帶來了一個黑暗時代。今天,債務動態正在對當今西方世界實施緊縮政策,將財產轉移給債權人,這些債權人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政府控制權來阻止對債務人的保護。
Polanyi關於“雙重運動”的樂觀理論認為,當社會變得過於剝削和兩極分化時,就會有一種將其重新社會化的反應。這是透過重建貨幣、交易和土地的公共監管來實現的,著眼於長期增長,而不是追求短期的金融利益。他期望社會主義提供作為人權的基本服務,前提是人民不應失去自由和權利作為滿足基本需要的代價:
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工業文明的一種內在傾向,即自覺地將市場服從於民主社會而超越自我調節的市場。對於產業工人來說,這是一個自然的解決方案,他們認為沒有理由不直接監管生產,也不認為市場在自由社會中應該不僅僅是一種有用但從屬的特徵。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僅僅是努力使社會成為一種獨特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努力的延續。
在他看來,“自由市場”政策導致瞭如此之多的貧困和壓力,以至於他們對加強社會監管產生了反應。這是牛頓第三運動定律的政治版本:每一個動作都會產生一個相等而相反的反作用。這就是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朝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革的本質:“社會保護自己免受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所固有的危險”(Polanyi,1944:76)。Polanyi預計,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帶來政治壓力,促使西方經濟走上二戰前似乎正在走的道路。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不能保證社會會自動地向前和向上發展。這種決定論關注的是潛力,即如果經濟體充分利用所有的知識,它們能夠實現什麼樣的目標。軍閥、債權人、地主和壟斷者在歷史上剝奪了人民技術潛力的成果。無論是Polanyi還是他那個時代的任何其他經濟未來主義者,都沒有把重點放在債務的指數增長上,將其作為推動私有化和逆轉進步時代(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是美國國家制度建設歷史上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轉折時期,其歷史背景是美國工業化所產生的種種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爆發)改革的槓桿。
Polanyi的“雙重運動”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團發起的反對改革以及贊成改革的反應。儘管二戰後英國和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蓬勃發展,但在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迎來了1980年後私有化和房地產市場放松管制的浪潮。今天的金融說客和他們的寵物學者主張政府幹預不是為了穩定經濟,而是為了防止像Polanyi的雙重運動這樣的社會反應。
所有形式的社會都管理著市場。關鍵是誰來管理它們,最重要的是信用關係以及政府權力與私人財富之間的平衡。將尋求貨幣收益從監管中解放出來在經濟上是兩極分化的,就像古代長期崩潰為農奴制使許多社會在許多世紀裡偏離了方向。Polanyi對社會歷史的貢獻表明,有必要在整個社會背景下監管金融、土地和勞動力市場,以保持繁榮而不是貧困。
Polanyi對交換模式的關注強調土地及其保有權應被視為一種社會制度,而不是一種商品。這與Marx的觀點並不矛盾。他的每個經濟階段都有自己的土地保有權模式以及勞動力在生產中的作用。自給自足的土地是古代公民和軍隊的基礎(直到他們因高利貸而失去土地和自由)。封建制度下,征服者以地主的身份佔有土地的租金。Marx預期,在工業資本主義下,土地及其租金將被社會化(Polanyi也將如此預期)。相反,金融資本主義下的房地產所有權已透過信貸被民主化,大部分土地租金以抵押貸款利息的形式支付給銀行家。
貨幣和信用模式也從古代經封建主義發展到近代。對債務和財政支付的價格和利率是被管理的,反映了青銅時代作為宮殿(或者古典古代向公民當局)支付手段的通用用途貨幣的起源。這是穩定的首要先決條件。在僱傭勞動力市場出現之前,高利貸成為獲得依賴性勞動力和小農土地的最早途徑。然而,美索不達米亞的統治者們宣佈清潔石板,要避免債務束縛和土地所有權的喪失,這不僅僅是暫時的。
羅馬皇帝們忙於發行法定貨幣,導致了價格通脹,原因是他們無力向富裕家庭徵稅——在帝國經濟日益萎縮的情況下,富裕家庭是唯一有能力支付的人。中世紀的國王同樣“貶低”了貨幣,試圖為他們的戰爭買單。另一種選擇是皇家債務的金融創新給銀行家和外國債券持有人。
當王室戰爭債務無法償還時,債權人要求礦產權、公共基礎設施和建立王室壟斷(如荷蘭、法國和英國的東印度和西印度貿易公司)。因此,金融成為公共領域私有化的主要槓桿,就像它在古代透過將土地“可出售”給富人並受制於掠奪性債權人的止贖,從而剝奪土地權利一樣——不可逆轉。
利率是“再分配的”,由政府制定。2008年後美國和歐洲央行推行的量化寬鬆政策下的債券和股票價格也是如此。五角大樓的資本主義並不像教科書中描述的是一個最小化成本的市場。它是按成本加成合同運作的,軍工企業透過最大化生產成本來增加利潤。
在今天倡導的“自由市場”的背後,是金融財富挪用政治、財政和中央規劃的力量,Polanyi、Marx和其他社會主義者希望看到這些作用擴充套件到民主政府手中。由此產生的房地產和債務工具的金融化市場,與一個世紀前改革者希望建立的截然相反。金融接管政府政策反映了資產剝離和經濟全面緊縮的商業計劃。
這不是Marx或Polanyi所期望的。如果這是西方文明金融化的市場動力所引領的,那麼它將是古代崩潰的重演,崩潰成為封建制度。
結束 和 相關閱讀
《論數字貨幣八大沖突》
《“天災”大流行如何摧毀西方》
《新經濟思想學會重磅討論:數萬億的Covid-19財政救助去了哪裡?》
《彼得·諾蘭:金融與實體經濟:中西方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發展》
《朱嘉明 | 改革四君子之一談中國改革四十年經濟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