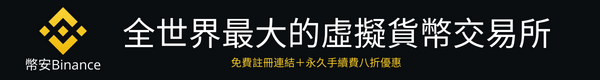這位獄友不僅沒有說明情況,還直接「反水」了,他說自己不知道我在用他的賬戶,自己的賬戶是被我給黑了。
之後,我在沒有經過正當程式的情況下,就在一個行政隔離部門拘留了13個月(律動注:Ross Ulbricht 自述也曾被關押於暗無天日的專門的隔離房間),這個案件也被移交給了聯邦調查局。有些人把這些設施稱為“黑色場所”,因為它們會讓被關進去的人與媒體、訪客和律師完全切斷了聯絡,大家對那裡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獄中的生活苦不堪言,一週洗三次澡,人被限制在一個8X10平方米的囚室裡,沒有空調,沒有風扇,也沒有足夠的通風。有一年夏天,我房間裡的溫度達到了華氏125度(約51攝氏度)。沒有任何證據支援那個獄友對我的指控,我希望回到普通牢房中,但我期望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你能想象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無法接觸到當下時代的任何資訊嗎?
走出時光機,重返現實社會
在服完漫長的刑期之後,出獄後的我在親眼目睹科技的發展後,感覺自己就像從時間機器裡走出來一樣。
我感覺自己被時間拋棄了,被新技術的發展和全球社會的發展驅逐了。作為一名駭客,我是名為“Electronik Tribulation Army”駭客組織的創始人和領導者。我過去常常與最新的玩意、開發和社會技術趨勢保持同步,還常常對惡意軟體進行反向工程,執行事件響應,並侵入幾乎所有無人關注的東西。
當然,在服刑期間,我也在報紙和雜誌上讀到了一些新科技內容,但說到底,我現在是一個外人了,一個對我曾經熟悉事物的局外人。如果你只是把這件事形容成老師變成了學生,只要重新學習就行,未免太輕描淡寫了。
不適應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最近,我收到了一臺新的戴爾 Inspiron 膝上型電腦,開啟熟悉的包裝,摸著它的感覺就好像是他鄉遇故知,但當我啟動它,迎接我的卻是 Windows 10。對於我來說,Windows 7 beta 版的釋出,彷彿就在昨天。我對 Windows 10 一無所知,完全不會使用。它有一個新的檔案系統,但我對它如何工作一點也不好奇。我想要做的,只是讓我的 Windows XP 恢復到原來的 Ubuntu Linux 和 Backtrack 3 雙啟動選項。
Windows 在系統控制的話語權上,比我更勝一籌:我不再能像以前一樣流暢而順利的操控這個系統了,我現在很討厭它。我花幾個小時在谷歌上搜尋如何解決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往往又是無功而返。我一次次挑戰這個討厭的系統,再被一次次的打敗。
還有一些事情,讓我難以接受。比如我不得不問我 12 歲的女兒,什麼是 # 話題標籤(hashtag),這太讓人尷尬了,「你不應該是個駭客什麼的嗎?」她對我說,這句話給像壓死我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十年裡,很多事情都變了。
在我那個時代,僱傭駭客被認為是一種禁忌,而現在,誰都可以僱傭駭客,甚至白帽駭客還可以透過發現漏洞獲得獎金,這些錢是合法收入的來源,也使白帽駭客已經成為一種職業。駭客們甚至在好萊塢電影、書籍和影片遊戲中被大肆渲染,諸如「Mr. Robot」這樣的駭客,在美國電視網路中被描繪成了英雄,不再是老套的網路惡棍。
一個我不再覺得與之有聯絡的世界
當我還在對過去熟悉的事物念念不忘時,世界卻在突飛猛進地前進。其實,我也在這個令人興奮的新世界之外觀察到的一些事情:
比如比特幣,它應該是世界上第一種加密貨幣,但我仍然不確定如何獲得或使用它們。
2007 年智慧手機出現,兩年後開始取代翻蓋手機,當我在電視上看到智慧手機廣告時候,我對著電視大喊「這是最愚蠢的事!誰願意把油膩膩的手指放在螢幕上?」但我錯了,每一個人都會這麼做,包括我。再比如,奧巴馬總統簽署了一項緊急控制網際網路的行政命令,網際網路的「死亡開關」由此誕生。這也是一件大事。
對於我曾經熟悉的網際網路世界,隨著 Arab Spring 到來,社會意識開始轉向使用 Tor 等工具和加密通訊平臺來保持網際網路的匿名性,端到端加密通訊開始流行起來。社交網站 Myspace 陷入了深淵,結束了我所知的那個建立個人檔案創造的時代,功利主義似乎已經是當今世界的預設理念。
比如 ZeuS. SpyEye. BlackHole 和 BackSwap 這樣的銀行業特洛伊病毒也流行了起來。隨著越來越多的裝置連線到網際網路上,可用的 IPv4 地址估計很快就要耗盡了。
一等兵切爾西·曼寧 (Chelsea Manning) 洩露大量美國國務院敏感電報之後,維基解密運動爆發了。駭客組織中的「匿名者」成為支援這場運動的重要參與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後來成了告密者,他向記者洩露了 9000 至 10000 份美國國家安全域性的絕密檔案,曝光了一個名為「稜鏡」(Prism) 的龐大間諜專案。美國政府仍在進行間諜活動,它一直會這樣。
大型廣告商正在收集使用者的各種資料,以達到內容營銷的目的。以前我也曾經竊取過使用者的資料。我知道這麼做違法,如果不是的話,我估計也給他們發一兩個廣告。
Facebook 和谷歌已經根植在網路使用者的日常活動中,智慧手機和汽車越來越受歡迎,當所有相互連線的裝置都無線連線到一個命令和控制裝置上,這無疑是駭客的戰場。亞馬遜的虛擬助理 Alexa 可能是一起謀殺案的目擊者,這些 AI 軟體一直在傾聽和記錄你的生活。
不確定的未來
對剛出獄的我來說,就像是踏入了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我再也看不到有意義的人際互動了,這個社會被喜歡、自拍、智慧手機和類似的技術攪得心煩意亂,在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常常讓我感到沮喪,因為我沒有跟著世界一起「進化」。我像是在時間之外的某個地方,鏡子的另一邊等待,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被釋放,重新融到社會中,我已經不瞭解面前的這個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