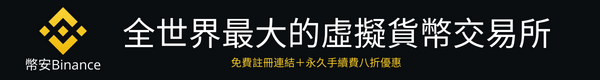196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參加了一場言論自由遊行活動。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空白的計算機打孔卡打上 FSM(free speech movement) 和 Strike 的字樣,掛在脖子上,以此來表達對集中式的官僚主義和權威的蔑視。
當時在計算機上程式設計還必須使用打孔卡[5],是手寫的機器程式碼,還沒有高階語言。這個時候 IBM 是計算機行業的大佬,也是制定打孔卡的實際標準。
那麼,當時這些伯克利的學生在遊行時,他們反對和爭取的究竟是什麼呢?除了言論自由,當時還有很多學生別了微章在胸前,然後仿照打孔卡使用說明書的語氣寫道,
我是加州大學的學生,請不要摺疊,扭曲旋轉或毀壞我。
所以,對這些生活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美國大學生來說,計算機作為一個隱喻,被看作是壓榨人性的機器。就像工業革命流水線上的機器,泯滅了人類的個性。這時候的計算機是一種反人性的技術,代表了集中式的官僚架構。
這種隱喻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很陌生的。今天提起計算機,我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計算機代表自由、個性化和虛擬社羣,代表點對點的連線,代表個人生產力的解放。就像喬布斯在蘋果電腦的廣告語上說的那樣,計算機是人類大腦的腳踏車,The bicycle of your mind。
如果把人類和其他動物進行對比,我們沒有豹子跑的那麼快,也沒有獅子那麼強壯,但我們人類懂得製造腳踏車和汽車這種工具,來幫助我們跑贏豹子,戰勝獅子。這時候計算機作為隱喻,反而變成了延展人類思維和創造力的一種工具,也是我們作為個體可以握在手裡的武器,就像印刷機和槍炮。
喬布斯注入蘋果電腦的這種思想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它也有一個更早的歷史來源。這種歷史來源叫做嬉皮士文化也好,更早之前可能還可以追溯到反越戰、搖滾樂、新公社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甚至是軍工學聯合體實驗室。這些歷史來源,實際上也解釋了,為什麼計算機作為一種技術,會從 60 年代的這種隱喻轉變成 90 年代的另一種隱喻。
如果不去看這些歷史來源的話,很多人會用一種相對片面的技術性的角度來解釋這種隱喻的變化。比如有一種解釋觀點是這樣的:
在 60 年代之前,計算機作為一種技術是以大型機的方式出現的,它的體積很大,需要塞滿整個房間,同時價格非常昂貴,只有政府、大學機構這些官方組織用得起,個人是觸碰不到的。而到了 70 年代之後,微型機技術已經開始慢慢出現了,計算機變成了可以放在桌面上的電腦,所以它慢慢就不是一種特權了,可以被個體所利用。
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忽略了文化層面的因素。比如計算機變小了並不意味著它就是屬於“個人”的技術。電視機同樣可以放在桌子上使用,但它自始至終帶著公共媒介的屬性。一個人對電腦這個工具的感受,他是怎麼理解這項技術的,這些不會因為體積縮小了就完全得到改變。另外,很多人可以透過網路連線在一起,也並不代表我們一定就要成為虛擬社羣。
《數字烏托邦》這本書提出的想法,是從時代和文化層面去追尋這種隱喻變化的深層次原因。也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些更早的歷史來源。所以,我們回到 20 世紀 60 年代的美國,看看當時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當時發生了哪些事情,使得計算機經歷了這樣一種改變。
反主流文化和賽博空間
有人認為,在二戰結束後, 20 世紀 40 年代和 50 年代,對美國人民來說,都是灰暗的年代。
一方面是因為 1947 年美國跟蘇聯開始冷戰,彼此陷入了經常性的核對峙局面。另一方面,美國在二戰時期建立了一個戰時經濟體制,提出了以軍事、工業、科學複合體為核心的組織結構,也就是所謂的“軍工學聯合體”。這種聯合體在戰時發揮了非常強大的力量,但到二戰結束之後,它逐漸演變成了一個嚴格的社會規則和官僚化的組織,它製造出了核武器,卻也把美國拖入了越戰的泥沼中。對人民來說,軍工官僚體系等同於一種權威性的、壓迫性的陰影。
所以 60 年代就成了一個個人探索和政治抗議爆發的年代。60年代恰好正值電視媒體普及,越戰成了第一場被直播的現代戰爭。美國國內很快爆發了各種各樣的抗議和反戰活動,大多數人把自己放在了這種權威的對立面,希望能推翻冷戰軍事工業的官僚體系。上文提到,伯克利大學的言論自由運動也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是一個生長在 60 年代的美國年輕人,尤其是白人年輕男性,剛上完大學,你那時候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呢?其實是明天蘇聯的核彈會不會直接扔了過來。加上 1961 年美國開始派兵介入越戰,當時有很多美國年輕人抱有這種末世的論調,他們覺得自己會是本世紀最後一代存亡的人類。整個美國社會也都籠罩在這樣一種戰爭與核彈毀滅的恐懼中。
而且這時候美國的中產階級經歷過大蕭條時代之後,個人財富已經慢慢迴流了,所以很多年輕的白人男性,他的生活條件是比較富裕的,但是心理上又整天受控於核彈的恐懼,於是精神世界出現了更多的反思,他們不希望畢業後進入僵化的系統裡淪為螺絲釘和工具,同時又不知道出路在哪裡,等於陷入了一整代人的迷惘情緒。1967 年上映的一部電影叫《畢業生》[6],反映的正是這種時代情緒。
史蒂夫·布蘭德(Steven brand),正是這千千萬萬個迷惘年輕人中的一員。1962 年從軍隊退伍之後,布蘭德迫切地想為心中的壓抑尋找出口,他走上了一段持續 6 年時間的遊歷體驗,每到一處便試圖找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很快他接觸到了一個藝術組織,名叫 USCO。這個組織聚集了很多藝術家一起進行全國巡演,並且共同生活了幾年。他們的表演方式很特別,不是在舞臺上單一地向觀眾傳達資訊,而是邀請觀眾參與進來,佈置各種各樣奇怪的現場,讓藝術家和觀眾共同體驗完成一個作品。USCO 喜歡技術神秘主義理念,同時也深受《控制論》的影響,在工作坊的背景下,推崇跨領域、多學科的協作。比如,他們會引入很多電子技術和工業產品來佈置現場,像是閃光燈、投光器、磁帶、幻燈片,甚至是迷幻劑、大麻和 LSD。這些小型技術和工具被當作是探索新的生活方式、體驗新的精神世界的一種工具。
布蘭德以攝影師的身份在 USCO 工作。在這裡,他接觸到了最早的新公社主義運動。當時美國很多年輕人也像他們這樣共同生活。為了逃避政府、軍隊和大公司的官僚機器,許多年輕人跑到農村建立公社,以集體生活的形式,實踐自己的理念和宗教信仰。他們自己動手建造家園,房子,水電,藝術,防衛,所有的一切全部自給自足,希望藉此建立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層級的社羣。
在此前的兩個世紀裡,美國人總共建立了500-700個公社,而這個時期則有數萬個公社成立,總共約75萬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公社成員認為自己是現代牛仔和印第安人,要開拓美國的邊疆,奔向開闊的平原,尋找更美好的生活。有意思的是,當時東方世界也有一場上山下鄉的運動,對應了西方世界的返土歸田(雖然兩者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
1966年,布蘭德意識到可以出版一本書,為散居在各個角落的公社提供生活所需的工具目錄和生存指南。更重要的是,為實踐公社生活的人提供精神世界的養料。於是,憑藉著剪刀、膠水,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編輯第一本《全球概覽》。這本書被喬布斯稱之為那個時代的 Google。資訊科技在《全球概覽》中佔有重要的位置,目錄不僅有工業產品和手工用品,也有機械和電子裝置,比如惠普的臺式計算機。就像藝術組織 USCO 那樣,新公社運動的參與者相信,包括計算機在內的小型技術可以用來探索新的生活方式、體驗新的精神世界,它也會改變個體意識和社會運作模式。《全球概覽》也將小型技術視為個體獲得自由的手段。
這種精神後面又傳遞到了駭客和程式設計師身上。在1971年《全球概覽》最後一期的停刊派對上,布蘭德邀請了500多人來參與這個雜誌出版專案的終結。他拿出兩萬美元的鈔票,邀請大家上臺講述自己的夢想,然後取走一部分現金去實現夢想。最後剩下 14905 美元被交給了弗雷德裡克·摩爾保管。這筆錢最後不知去向。但摩爾和另一位朋友在 1975 年春天共同創立了“家釀計算機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包括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布蘭德爾後還幫助籌備了第一屆駭客大會,參會的人就有 Richar Stallman。
最後一期《全球概覽》
《全球概覽》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啟發的年輕人不僅有喬布斯,還有凱文凱利,以及發明了圖形化介面等一系列技術的施樂帕羅奧托研究中心工程師。這批人後面成了產業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們有的成了偉大的創業者和企業家,有的成了發起自由軟體運動的駭客,有的則像凱文凱利這樣成為了重要的記者,推動了《連線》雜誌。最終這批人共同孕育了今天的矽谷文化。
除了《全球概覽》,布蘭德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創辦 WELL 線上論壇。1984年賽博朋克小說家威廉·吉布森發表了小說《神經漫遊者》,首次創造了“賽博空間“這個詞。而在 1990 年,計算機評論家巴羅根據自己在 WELL 論壇上的經歷,第一次提出用“賽博空間”這個詞來描述剛剛出現的電信與計算機網路的交叉路口。
這個新的賽博空間被具象為一個“電子邊疆”。就像60年代末新公社運動的成員們試圖在美國鄉村創造一個烏托邦社羣,賽博空間也被想象成了一個崇尚平等與自由的新社會。在這個閃閃發光的電子宇宙裡,他們試圖拋棄政府、法律和武力,構建一套新的秩序。巴羅宣稱,“你們關於財產、表達、身份、遷徙的法律概念及其情境對我們(賽博空間)均不適用”。
相同的精神核心
如果要對這一連串的歷史進行總結的話,它最本質的精神核心,用一句話來表達是:
藉助個人化的技術和工具,讓個體從僵硬的社會體系和冰冷的國家機器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免於被奴役。
這種個人化的技術和工具,既包括一個揹包和一頂帳篷,也包括計算機和網際網路。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個人化的技術和工具往往不是突然出現的,恰好來源於鬥爭的對立面。60年代的言論自由運動及新左派都曾正面跟美國的軍事、工業與學術界進行對抗,但 USCO 的藝術家、嘗試致幻劑的嬉皮士、參加新公社運動的年輕人,他們實際上都接受了技術樂觀主義、資訊理論,以及冷戰時期軍工學聯合體在研究領域興起的跨界合作文化。
事實上,《數字烏托邦》這本書提出的最重要的論點,正是反主流文化運動以及後續的賽博文化,他們最早的種子也來源於自己所反對的軍工研究文化。正是在最早的軍事協作研究中,一批跨學科、跨領域的人被聚集了起來,科學家、工程師、大學教授、創業者,他們在一個彼此沒有等級制度、可以自由交流協作的環境中,創造出了一批影響世界的技術:核武器、雷達、網際網路的前身 ARPANET、計算機、《控制論》、《資訊理論》等等。儘管反對冰冷的軍工機器,但布蘭德那個時代的學生都深深迷戀上了軍事協作研究的知識產物。
新左派年輕人在核彈與戰爭的陰影下長大,但他們也在一個物質財富快速增長的美國社會中長大。參與言論自由運動的大學生在攻擊工廠時,這些工廠也在生產滿足年輕人各種需要的產品。在反對主流文化的同時,新公社運動和《全球概覽》展示了另一種出路:年輕人們可以拿工業化社會的產品作為一種工具,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意識,去變革集體社會的運作模式。
這種方法以《控制論》和《資訊理論》為通用語言和指導思想,強調更自由的社羣,推崇個人化的工具和技術,鼓勵跨學科協作。它最早來源於二戰時期美國的軍事研究文化,只是隨著戰後秩序的重建,軍工學聯合體逐漸變成了僵化的官僚結構,最終成為了反主流文化運動的靶子。這也是為什麼計算機作為60年代到90年代間最重要的一種工具,會從“國家機器統治力量的延伸”這樣的隱喻,最終轉變為另一種反體制和爭取個人權利的象徵。
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今天程式設計師和駭客社羣會流行宗教文化,對於自己所使用的程式語言和編輯器等工具,會陷入無休止的崇拜與鬥爭,而不能像對待一個普通的物件那樣去對待它。因為在很久以前,工具對他們而言,真的不止是工具而已。
60年代以來的這部分歷史,工具和技術曾與“改變意識形態”、“探索新理念”牢牢地綁在一起。這種精神傳統從新公社運動的那批年輕人身上慢慢流淌到了駭客與程式設計師身上,融入了自由軟體運動、開源運動,賽博空間中誕生出了密碼朋克,最終這部分精神又一次傳遞到了區塊鏈身上。
是的,我當然願意相信,區塊鏈也是這種個人化的技術和工具。它是幫助我們建立新家園的小型技術,可以改變個體的思想和意識,變革集體社會的運作模式。一切的宗旨,都是為了讓個體從僵硬的社會體系和冰冷的國家機器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免於被奴役。
今天我看到區塊鏈行業的人在建立 DAO,在建設 DeFi,看到無數自由市場主義的人把比特幣作為一種去中心化的貨幣或者數字黃金,這一切跟當初那些看著《全球概覽》跑到鄉村建公社的年輕人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為了掌握私人資產、記下比特幣的私鑰,跟在公社蓋房子、搭建網格穹頂的行為沒有本質區別。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寫到這裡,我想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又會發生什麼?
環顧四周,我們在 2008 年擁有了比特幣,在 2014 年擁有了以太坊,隨後建立起了一系列加密經濟的基礎設施:DeFi、DAO、Web3、NFT......這個新的電子宇宙在悄然生長。而在這個獨立的世界之外,一個更大的世界同樣在發生劇烈的變動。
從 2019 年以中美貿易戰為象徵的“新冷戰”,到 2020 年一場蔓延全球的前所未有的病毒危機,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趨勢伴隨著新的金融危機興起,人們稱這一年是過去十年最糟糕的一年,但也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與此同時,傳統網際網路世界已經高度發達、巨頭林立,但賽博空間的發展卻沒有如設想中那樣使人更自由,反而促進了監控技術的發展,創造了稜鏡門和環形監獄。
同樣,我也不禁聯想到中國自己的情況。這輛高速列車以每年 10% 的增長速度瘋狂向前奔跑,從未停下,直到 2020 的疫情按下了暫停鍵,人們終於能停下來好好想想“我們究竟是要奔向哪裡”。
過去 20 年,一箇中國年輕人最好的職業是公務員;20 年後,是成為一個影片 UP 主。這批新畢業的年輕人,他們以前在成長過程中是怎樣認識這個國家的,被暫停減速後,又要怎樣修正過去這些認識?
經歷社會財富快速增長的過去,迎接只會更壞的未來,會不會讓新一批的年輕人陷入悲觀的論調。面對逐漸強大的國家機器,他們是否也會對“成為這個龐大體系的一部分”產生恐懼,質疑層級結構是否會摧毀個人精神?尤其是當整個國家自己也需要應對國際形勢的惡化和對外的挑戰。
中國會不會也有一次反主流文化運動,人們手中能掌握的小型技術,作為個人化的武器和工具,又能有哪些?我能想到的似乎就只有區塊鏈了,VR 和 3D 列印或許也是一部分,但它們都能沒發展起來……熱門的 AI 甚至應該是站在了反面。
在 1996 年釋出《賽博空間獨立宣言》[7]時,巴羅在結尾這樣寫道:
我們將在網路中創造一種心靈的文明。但願她將比你們的政府此前所創造的世界更加人道和公正。
今天這句話,同樣值得送給在座的所有從業者們。
參考資料
[1]密碼朋克: https://www.huxiu.com/article/269132.html
[2]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E1MzQ3MA==&mid=2450143058&idx=1&sn=34eceb133986e096162e348b094259ed&scene=21#wechat_redirect
[3]《數字烏托邦:從反主流文化到賽博文化》: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1632268//
[4]《大教堂與集市》: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881855/
[5]打孔卡: https://www.landley.net/history/mirror/pre/fsm.html
[6]《畢業生》: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292271/
[7]《賽博空間獨立宣言》: https://www.eff.org/cyberspace-independence